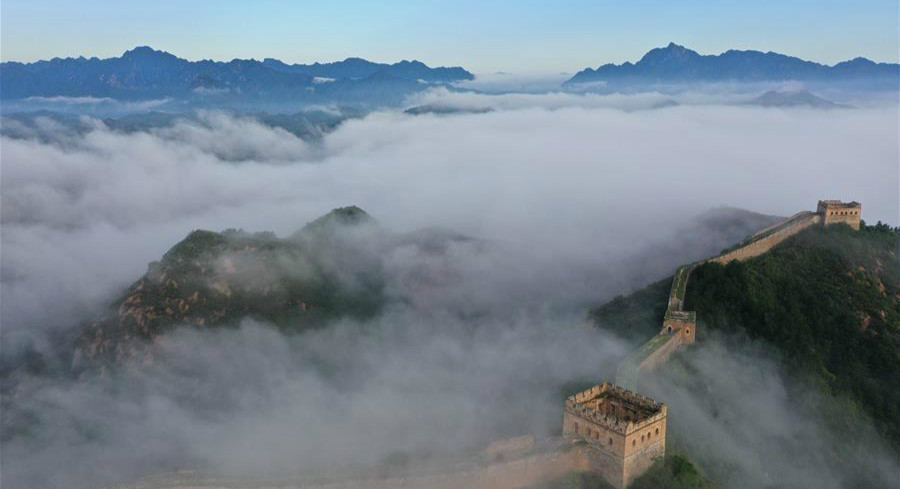|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对公开的内容、渠道以及责任主体做了明确,提出要以“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过程中社会关注度高的信息”为重点,“尽可能对外公开”。 在“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的政务透明原则语境中,对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过程中的信息重申“尽可能对外公开”的底线,“尽可能”或许不算严格的行政公务措辞,公众却也从中读到了官方推动重大建设项目审批、实施相关信息予以彻底公开的决心。国务院此番发文力推,循着行政权力的具体触角做改革策动,“能公开的尽可能公开”,此处对于公开诚意和力度的描述有赖公众参与予以充分实践和验证。 重大建设项目与民众切身相关的元素,除了公共建设成果为社会生活提供的便捷,还有可能因为工程建设过程对公民个体形成的某些直接影响,包括噪音污染、生态干预以及可能的土地纠纷。政府决策重大建设项目的各项步骤,是在项目动工、引起民众关切之前,更便于满足公众知情的前置程序,一系列决策、审批程序和结果的依法公开,有助于公民参与的提前介入,并因此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增强官民沟通的有效性。此次国务院文件对具体的信息公开主体做了责任明确,可以说进行逐一点名,谁批准谁公开,谁招标谁公开,谁为工程项目划拨土地谁就负责公开相关流程的政务信息。按照重大建设项目不同阶段政务信息产生的责任主体明确信息公开义务,有助于不公开时的责任追究,也有助于民众按图索骥提出信息公开诉求。值得注意的是,分阶段明确信息公开责任,同样需要确保相关公开信息的统一呈现,无论是信息公开的平台建设,还是基于便于公众查询、参与监督的公共诉求,公开信息都需要更加强调其可查询、易查到的公共属性。 政府信息公开的内涵,有政府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大类。此次国务院新规推动重大建设项目的主动公开,首在约束政府审批、重大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决策程序规范化,也同时为公民监督政府作为给出明确的权利保障承诺。行政权力运行应遵循“法无授权即禁止”原则,从义务层面也要看到,并非法无明文就意味着可以不作为,恰恰相反,国务院此次特别对重大建设项目决策、实施信息做刚性具体的公开要求,其价值除了重申和明确透明的意义,更在于具体化列名那些必须公开的事项,并以“尽可能公开”做兜底约束,向政府部门“不强求就不公开”的惯性思维开刀。更强硬的措辞、更明确的范围列举,国务院大张旗鼓督促重大建设项目的公开进程意在掀起重大项目之外的政务公开浪潮,进一步挤压政府主动公开层面的所谓“对策空间”,拓展公民主动伸张知情权的权利范围,这也是本届政府反复重申、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转型的用心所在。正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言,“公开透明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目标,一个不会说、不及时说、不充分说、不坦诚说的政府,不可能适应民主政治需要,满足公众知情诉求。”(2016年5月15日中国政府网)在信息公开问题上,“说”本身就是“做”。 “尽可能公开”可见国务院新规推动透明化政府的诚意,其中对于“可能”的能力评估和定义则依然有赖司法裁量的最终判断。哪些信息处于能公开却并未公开、拒绝公开的范畴,国务院作为最高行政权力机关有厘定和裁决的职责,以果断、明确的行政复议结果推动信息公开的落地,而司法在审理信息公开案件时的居中判断,更需要执行层面对司法权威的尊重与敬畏。明确的公开范围,需要更加明确的问责机制作为制度保障,正因为有“不公开就担责”原则的刚性贯彻,信息公开所指向的透明政府价值才有申明的可能性和操作意义,“尽可能公开”才不至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身陷被人为定义的处境。 作者:南都社论 |